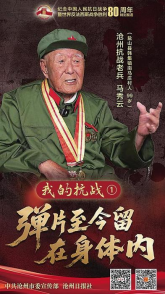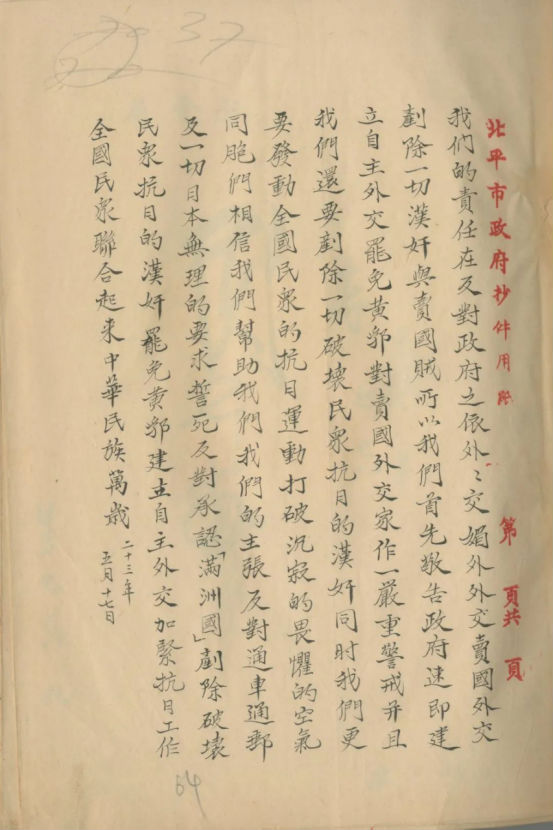抗战在保定:人民战争的伟大实践与智慧结晶
9月2日,位于保定市清苑区的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内,人流不息。
参观者指尖轻抚斑驳弹痕,80年前的呐喊仿佛仍在巷道深处回响。冀中平原的黄土之下,埋藏着一部用勇气与智慧书写的抗战史诗。
全民族抗战期间,保定作为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,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战场。地道战、地雷战、麻雀战……保定军民以无穷智慧创造出变幻莫测的战术,如同一把插进敌人心脏的尖刀;在以阜平为中心的晋察冀边区,战斗与建设并行,军民同心抗敌,凝聚起非凡的创造力。烽火岁月里的抗争与智慧跨越时空,至今仍在历史星空中熠熠生辉。
从地道战到地雷战:屡创奇迹的作战“法宝”
青砖灰瓦的街巷静立如初,十字街口的老槐树虬枝盘曲。远处高架桥上,“地道战,克敌制胜的创举,人民智慧的结晶”一行金色大字,铭刻着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记忆。
“宁绕黑风口,不从冉庄走”的顺口溜,至今仍在诉说着保定人民以智慧克敌的传奇。
“您看这口普通的锅台,底下就是地道入口。”保定市清苑区地道战遗址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王静宇掀开铁锅,露出仅容一人通过的洞口。在冉庄,这样的机关无处不在:碾盘下的暗格、墙根的夹缝、水井的侧壁……几乎每一处生活场景里,都可能藏着通往“地下长城”的秘密通道。
七七事变后,侵华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残酷、疯狂的大“扫荡”。华北平原无险可守,保定军民灵活运用毛泽东游击战思想,创造出各种克敌制胜的巧妙战法。
98岁的冉庄抗战老兵李恒彪回忆:“起初挖地洞只为藏身,只有一个口,敌人一堵就死。后来留两个洞口,再后来连成地道网。”凭双手和镢头,冉庄军民挖出以十字街为中心,总长16公里的地道系统,实现“户户相连、村村相通”。
以地道为基,保定军民还筑围墙、留小路,高房建岗楼,民房搭天桥,形成“房顶、地面、地道”三层交叉火力,再以野外地道串联,构成“立体作战阵地”。正如时任冀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在《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》中指出:“地道既适于隐蔽,又适于进攻,这才是完善的战斗地道。”
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,仅冉庄军民就利用地道作战157次,毙伤敌人2100余名。
日军的梦魇不仅是四通八达的地道,还有如影随形的地雷。这些土地雷是保定军民就地取材,用铁皮、石块做雷壳,用火柴头、硫磺配炸药,用动物粪便掩盖地雷气味,用陶器制作地雷躲避探雷器,等等。拉雷、踏雷、连环雷、头发丝雷等数十个品种,让地雷“追着敌人跑”。地雷战被日军称为“最可怕的战术”,其经验被写入八路军《游击战争指导纲要》,并推广至华南、华东敌后战场。
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更在保定铺天盖地展开。游击队化整为零,开展麻雀战,忽聚忽散,袭扰消耗敌人;开展破袭战,扒铁轨、炸桥梁、割电线,瘫痪日军交通命脉。在白洋淀,雁翎队利用芦苇荡港汊优势,驾小船神出鬼没,伏击汽艇、智擒敌船,书写了“水上游击战”的传奇。
这种以分散配置、灵活机动、袭扰消耗为主要特征的游击战,以“草木皆兵”的威慑力,让侵略者胆战心惊。这些经典战术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“人民是真正的英雄”。它们没有先进的技术,却凝聚着劳动人民的智慧;没有庞大的军工体系,却依靠军民同心的力量,在保定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血肉长城。
从黄土岭战斗到百团大战:统分适度主动歼敌
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,晋察冀边区抗日军民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洛川会议制定的战略方针,以游击战与运动战紧密结合的灵活战术,开创华北敌后抗战的崭新局面。
1939年大龙华战斗前夕,八路军通过周密侦察,准确研判日军企图打通涞易公路、割裂北岳与平西联系的战略动向。杨成武据此制定“一路主攻、三路打援”的作战方案,体现出超前布局、主动制敌的战术预见力。
战斗结束后,八路军缴获50余册日军机密文件。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评价:“你们缴获的这批文件很重要,比缴获敌人几百支枪、几门炮的胜利还大。”
“情报先行,知彼知己;巧用地利,以弱克强。”保定市方志馆副馆长冉白正说,面对装备精良、阵型严整的日军,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善用地理空间实施动态部署,实现“分散可隐蔽、集中能歼敌”的作战效能。
作为抗日战争中经典的山地伏击战,1939年11月的黄土岭战斗里,八路军采取“诱敌入瓮、据险伏击、牵制增援”的战法,将敌军诱至保定涞源县黄土岭以东的峡谷地区。这条峡谷犹如一条长约2.5公里的“天然口袋”,最宜设伏。
待日军完全进入伏击区域,部队依托制高点发动突袭,击毙号称“名将之花”的日军中将阿部规秀,使敌军陷入“虽装备精良却无法还击”的绝境。
“击毙日军中将指挥官,这在华北战场是第一次,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也是第一次。”冉白正说。
同一时期,保定抗战军民灵活运用游击战与运动战,依据战况实时调整战术,屡建奇功。
1943年秋,神仙山保卫战期间,面对多路进攻的日军,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42团团长成少甫果断决策,集中兵力打击敌之一路,优先重创南面进犯之敌。
敌攻暂缓后,八路军迅速撤离原阵地,协同民兵在山路广泛布设地雷。果然,日军再次进攻时,先头部队刚入“十八弯”首弯即触发地雷,攻势顿时溃乱。
同样打击日军的还有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涞灵战役的关键一战——东团堡战斗,全歼日军士官教导大队170余人。《聂荣臻元帅回忆录》中记载:“东团堡之战,是以顽强对顽强的典型战例,充分显示了我军的战斗力,对敌人震动很大。”
“东团堡战斗时,日军的武器有迫击炮、重机枪、轻机枪等,并在据点外围做了地堡、围墙、外壕等很多防御。在这种情况下被八路军全歼,给敌人带来的打击不仅仅是失去一支精锐的种子部队,更是打压了他们的武士道精神。”涞源县文保所原所长安志敏说。
从东西庄阻击战、大龙华突袭战,到黄土岭战斗、神仙山保卫战,保定军民不仅大量歼灭日军有生力量,更以一系列实战创新与无穷智慧,书写人民战争史上的辉煌篇章。
从民主建设到文化繁荣,战火中锻造模范根据地
2012年12月29日至30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阜平考察时指出:“阜平是一个拥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地方,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创建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——晋察冀根据地的首府,是晋察冀边区政治、军事、文化中心。”
1937年11月18日,晋察冀军区机关迁驻阜平,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以阜平为中心创建起来,并被誉为“抗日模范根据地”。
“面对日军对根据地残酷的‘扫荡’‘蚕食’,在军事斗争基础上,边区开展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的探索与建设,牵制、抗击和消灭日军大量兵力,对于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和全国持久抗战发挥重大作用。”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资料科科长栗静介绍。
“黄豆豆,豆豆圆,咱村选举村议员……一颗黄豆搁在碗……她碗里的黄豆乒乓落……俺活七十头一遍。”诗歌《豆选女县长》曾在晋察冀边区流传,描写的是边区民主选举中,不识字的百姓用一颗颗黄豆选出唐县第一位女县长陈舜玉的故事。
1940年7月至10月,边区开展大规模民主选举运动,构建起完善的民意与行政机关体系,建立新民主主义“三三制”政权,从政治上团结和凝聚最广泛的抗日力量。
“‘三三制’,即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,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,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,中间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。这样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,成为巩固和发展边区、坚持持久抗战、争取最后胜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,同时也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积累宝贵经验。”冉白正说。
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,聂荣臻签发“树叶训令”,禁止部队采摘村庄附近的树叶与民争食,要求把树叶留给群众果腹。这一纸训令,深刻体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、休戚与共的深厚情谊,成为党的群众路线和优良作风的生动见证。
边区的模范作用,同时还体现在经济和文化领域。
1938年3月20日,设计成型于安国、印制于阜平法华村的第一张边币在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。这张红色底纹、图案为“小黑马耕地”的一元边币被群众亲切地称为“抗日票”“红票子”。
打击日伪票及各种杂钞、反抗经济掠夺、发放救灾贷款、帮助群众及时恢复生产、支持边区经济发展……从1938年成立到1948年与冀南银行合并组成华北银行,晋察冀边区银行通过发行自己的货币,创建敌后“经济抗战”的特殊战场。
“八匹骡子办报纸,三千字内著文章”,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创刊最早、坚持时间最长的报纸,《晋察冀日报》从1937年12月11日创刊,到1948年6月14日终刊,共出版2854期,被誉为“边区喉舌”和“抗战文旗”。晋察冀新闻战线上,涌现出以邓拓、沙飞等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红色新闻人。
与此同时,晋察冀边区文艺工作者以文艺为枪,创作大量诗歌、戏剧、小说、报告文学、歌曲等反映边区斗争等内容的作品。孙犁的小说《荷花淀》、曹火星的歌曲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、田间的街头诗《假使我们不去打仗》、丁里的多幕话剧《子弟兵和老百姓》等文艺创作,在民族解放事业里起到团结人民、打击敌人的巨大作用。
巍巍太行,见证了一段烽火岁月,见证了这场伟大胜利。
抗战时期,保定人民累计参军人数超过20万,参战人次近百万。在这片英雄土地上,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书写了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。
80载光阴流转,昔日黄土岭上,八路军炮火精准破敌的军事智慧,已沉淀为今日破解乡村振兴密码的创新实践;当年大龙华战斗中军民同心协力的动人场景,已演绎为现代开发区厂房里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生动画面;而阜平这片红色沃土,已成功摘掉贫困的帽子,正凭借山地农业与生态旅游的深度融合,走出一条革命老区的振兴之路。
今日保定,传承红色基因,置身于伟大时代。保定人民正以同样的勇气与智慧,加快打造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中的现代化品质生活之城。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,视死如归、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,不畏强暴、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,百折不挠、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——伟大抗战精神已融入保定血脉,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,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续写新时代的荣光。
相关推荐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