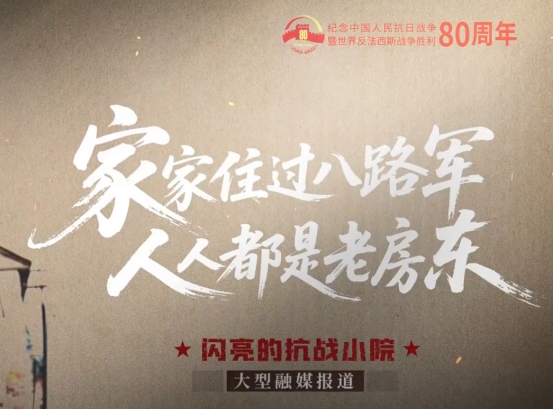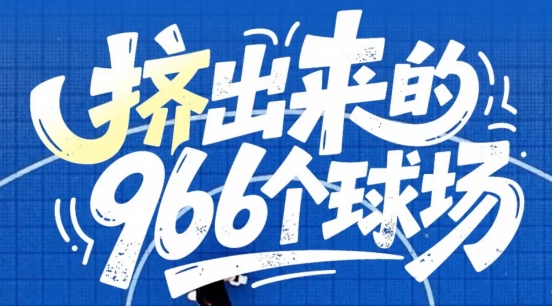瞭望丨宝藏正定看文脉
◇承载中华千年古建之美,亦是传统文化的无声见证与活态传承
◇以碑刻、鉴藏、书法为载体,传承中华艺术风韵与精神风骨

正定古城夜景(2025 年 5 月 15 日摄)
若想寻访一座“步步有历史,寸寸有文化”的宝藏之城,正定便是绝佳之选——在不足9平方公里的历史城区内,密集分布着1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“国宝”密度之高,在全国县级行政区域中首屈一指。
正定之美,美在古城肌理;古城之魂,魂在文化根脉;文化之韵,韵在文物传承。漫步其间,古塔古建的一砖一瓦间,流淌着唐风宋韵的千年回响;名碑法帖的一笔一画里,镌刻着侠骨柔情的文脉基因。这里的每一处遗存,都是可触摸的文明密码,让“宝藏之城”的称谓有了最生动的注脚。
建筑凝固“中式美”
正定古城承载中华千年古建之美,建筑是凝固的中式艺术,亦是传统文化的无声见证与活态传承。
“遥瞻恒岳青霞绕,静对滹沱白练长。”河北正定西依太行、南傍滹沱,作为拥有1600余年历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,古称常山、真定,素有“燕南古郡、京师屏障”之称。自晋代至清末,这里始终是区域中心,明清时期更与北京、保定并称“北方三雄镇”,奠定了其历史地位。
源远流长的历史为正定留下了“九楼四塔八大寺,二十四座金牌坊”的盛景。尽管历经战争、风雨与地震,古城内仍现存隋唐以来古建筑38处,以“九朝不断代”的连续性被誉为“古建艺术宝库”。梁思成曾三访正定,惊喜于其古建筑的丰富珍贵;他的学生、古建专家罗哲文亦评价其隋碑、唐代木构建筑、宋代建筑群、唐宋塔及元明清历代遗存皆“有物可看,有迹可循”。
开元寺作为正定古城“八大寺”中最古老的寺院,其遗址上矗立的钟楼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。该钟楼通高14米,为二层阁楼式建筑,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唐代钟楼,也被称为现存“三座半”唐代木构建筑中的“半座”。
1933年,梁思成首次考察正定时便发现了这一“意外收获”,他在《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》中记载:“上层外部为后世重修,但内部及下层雄大的斗拱,若说它是唐构,我也不能否认。”那时,国内尚未发现唐代建筑,有外国学者声称中国已无唐代建筑。1988年落架重修时,木构件题记进一步证实其建于唐代,为中国唐代建筑研究提供了珍贵实例。
在正定古城南北中轴线上,原址复建的阳和楼巍然矗立,被誉为“镇府之巨观”。梁思成曾对其进行详细测绘,并盛赞其“庄严尤过于罗马君士坦丁的凯旋门”。这座建筑不仅是古城的地标性遗存,更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恢宏气度。
正定还是元曲艺术的发祥地与繁盛之城,“元曲四大家”之一的白朴在此度过了大半生并创作了大量作品。相传,他的许多经典剧目曾在阳和楼“首映”,使正定成为元曲文化传播的重要舞台。
如今的阳和楼,河北梆子的高亢唱腔时常回荡,穿越千年历史,响彻古城街巷。梅花奖获得者、河北梆子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彭蕙蘅近年常带学生在此演出,以“传承正定戏曲文脉”为己任,让古老艺术在原址焕发新生。
阳和楼下,钢化玻璃地面下清晰可见累代叠压的原有楼基砖构,行人迈步其上,仿佛“平步”历史烟云。楼前广场已成为居民游客的共享空间:茶余饭后,人们或把麦放歌,或伴乐起舞,昔日元曲兴盛地,如今化身充满烟火气的百姓大舞台,古今文化在此交融共生。
作为正定古建遗存中最负盛名的代表,隆兴寺以“京外第一名刹”之美誉成为古城的骄傲与象征。其始建于隋开皇六年(公元586年),初名龙藏寺,唐代更名龙兴寺;北宋时,宋太祖赵匡胤敕令铸大悲观音菩萨金身、建大悲宝阁,并依宋代《营造法式》扩建为中轴线布局的宏大建筑群;元明清三代均有修葺,清康熙年间定名隆兴寺,因寺内铜铸大菩萨像俗称“大佛寺”。这座历经千余年的寺院,完整保存了宋代建筑规制,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“凝固艺术”典范。
寺内造型奇特的摩尼殿,是国内现存唯一一座北宋“十字”造型建筑,其平面布局与建筑形式在中国古代殿堂中独树一帜。梁思成在《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》中盛赞:“十字形的平面,每面有歇山向前……这摩尼殿重叠雄伟,可以算是艺臻极品。”这种在宋画中常见却现实罕见的形制,使其成为宋代建筑艺术研究的重要实证。
大悲阁内矗立着北宋铜铸千手千眼观音像,这尊我国现存最高大、最古老的立式铜铸佛像,与沧州铁狮、定州塔、赵州石桥并称“河北四宝”。如今,阁前常有年轻舞者演绎《千手观音》,悠扬音乐与急促鼓点中,古典佛像与现代艺术交融,为游客带来兼具文化底蕴与视觉冲击的体验,让千年古刹焕发当代活力。
为推动古建文物的“活态传承”,隆兴寺景区通过多元举措拉近传统文化与公众的距离:重要节假日常态化举办舞蹈、茶艺等沉浸式文化活动,让游客在古建氛围中感受艺术魅力;文旅部门推出门票优惠政策,同步完善服务设施,并开发古建研学项目,引导公众深入了解建筑美学与历史底蕴。这些措施不仅让千年古刹成为“可感知、可参与”的文化空间,更实现了从“文物保护”到“文化共享”的深度转化。
碑帖镌刻“丹青香”
正定以碑刻、鉴藏、书法为载体,传承中华艺术风韵与精神风骨,成为连接古今的文化地标。
隆兴寺内一座不起眼的亭子里,安放着被誉为“隋碑第一”“楷书之祖”的《龙藏寺碑》。此碑刻立于隋开皇六年(公元586年),通高3.15米,碑文正面楷书1400余字,碑额浮雕六龙相交,尽显隋唐古朴风格。其书法方整清秀,上承南北朝余韵,下开初唐诸家先河,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典范之作。
全国现存隋碑稀少,《龙藏寺碑》的完好留存,离不开正定县前瞻性的文物保护实践。上世纪80年代初,因地处低洼、长期受自然侵蚀,石碑风化严重,一度濒临损毁。正定县领导高度重视,由时任文化局局长贾大山牵头推进保护工作。
为实现“万无一失”,贾大山率文保团队多次赴国家及省市文物部门沟通,并在国家文物局专家指导下,最终通过垫高地基、加装防风挡雨保护罩等精准措施,使这块隋代书法瑰宝得以妥善留存。如今,历经岁月洗礼的《龙藏寺碑》,字迹清晰,见证着中华文脉的延续。
同一时期受到保护的,还有一度湮没于荒烟蔓草间的朱熹“容膝”碑、赵孟頫“本命长生祝延碑”等碑刻。
除书法名碑外,正定文化史上另一耀眼标签当属梁氏家族及其“蕉林书屋”。如今,古城繁华街区中新修缮的“梁氏宗祠”与“蕉林书屋”已免费开放,院壁《蕉林书屋歌》石刻静静诉说着这座藏书楼的千年传奇。
自明代重臣梁梦龙起,正定梁氏“四世显贵”,直至清代鉴藏大家梁清标。仕途归隐后,梁清标改建曾祖父别墅为“蕉林书屋”,潜心书画鉴藏。经几代人倾力搜求,书屋巅峰时“蓄古书数十万卷”,以“项家蕉窗梁蕉林,图书之富甲古今”享誉天下。
明清易代的动荡中,无数文化珍品散佚飘零,梁清标以超凡鉴藏眼光抢救保护,《千里江山图》等传世瑰宝均曾为“蕉林”旧藏。其“手泽存先志,功勋在古人”的诗句,道破收藏初心——非为私藏,而在传承文脉。
近年“盛世修典——‘中国历代绘画大系’成果展·蕉林遗韵特展”巡展全国,百余幅梁清标旧藏打样稿,包括《百花图》《簪花仕女图》《韩熙载夜宴图》等集中亮相,让这份跨越数百年的文化守护,在当代续写新篇。
若说碑刻书画传承中华艺术风韵,那么源于正定的颜真卿《祭侄文稿》,则以笔墨镌刻着民族精神风骨。这幅被誉为“存世颜书第一”“天下行书第二”的法帖,诞生于一段悲壮的历史记忆。
唐“安史之乱”中,安禄山叛军围攻常山(今正定),镇守此地的常山太守颜杲卿(颜真卿从兄)率子颜季明浴血抵抗。城破被俘后,叛军斩颜季明头颅逼降,颜杲卿骂贼不绝,惨遭钩舌肢解,30余颜氏族人一同殉国。千里之外的颜真卿寻得侄儿头颅,在悲痛欲绝中写下这篇“血泪交迸”的祭文——墨迹随心绪起伏,涂改处可见悲愤难抑,线条遒劲如剑,被誉为“不是书法作品的书法绝唱”。
这段忠烈往事,正是历史典故“常山舌”的由来。文天祥被俘后在《正气歌》中以“为颜常山舌”赞颂其气节,在途经正定时更赋诗“人世谁不死,公死千万年”。如今,正定子龙广场的浮雕墙上,《祭侄文稿》与历史名人共列;博物馆中的复制品前,游人仍能从跌宕的笔墨间,触摸到那份穿越千年的家国赤诚。

游客在正定古城游玩(2024 年 9 月 16 日摄)
古塔映照“人文情”
正定古城通过代代相传的文物保护实践,成为中华文脉薪火相传的生动见证。
从正定南城门远眺,古城天际线中最引人注目的,当属造型奇绝的广惠寺华塔。这座始建于唐代的古塔高33米有余,具有极高的历史、科学、艺术价值。梁思成曾评价其“若由形制上看来,这华塔也许是海内孤例”。
华塔上半部以八角八面布局为骨架,交叉塑有力士、海兽、佛、菩萨等艺术形象,花饰繁复而韵律井然,远观如绽放的巨型花束,故初名“花塔”(古时“花”“华”通用,后称“华塔”)。塔体不仅可供登临远眺,更留存着宋人题刻、金人墨书及乾隆帝巡幸题诗等遗迹,堪称立体的历史文献。
如今,灰瓦红墙的华塔已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化地标,塔外生民街商铺林立、烟火繁盛,千年古塔与市井繁华相映,续写着“古韵与新声”的当代对话。
华塔旁静静矗立的烈士纪念碑,诉说着一段文物保护与家国大义交织的往事——这座千年古塔的完好存世,离不开“护塔烈士”赵生明的牺牲。
1947年8月24日凌晨,第二次解放正定战役打响。晋察冀军区战士在突袭进城后,遭遇残敌逃入广惠寺华塔负隅顽抗,据守二层平台扫射。此时若以重武器强攻,残敌可速歼,千年古塔却将化为瓦砾。时任副团长的赵生明毅然下令:“禁用炮轰,改用轻武器!”激战中,华塔得以保全,30岁的赵生明不幸中弹牺牲。
战后,晋察冀军区追授其“大功功臣”,正定人民将他牺牲所在的南门里街更名为“生明街”,后演变为“生民街”。1984年,赵生明烈士纪念碑迁至广惠寺遗址院内,与他用生命守护的华塔永世守望,成为“丹心护文脉”的精神坐标。
文物背后,镌刻着守护者的身影。1933年,时局动荡中,梁思成携林徽因等以“为国存史”的使命感,两次赴正定开展抢救式考察。他们克服艰辛,以镜头、笔墨与图纸记录下古建筑的真实面貌,撰写的《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》,为彼时濒危的“国宝”留存了珍贵的“建筑基因密码”,也为后世保护奠定了权威基石。
这份严谨与执着穿越时空:2015年,正定在隆兴寺方丈院(梁思成当年借居处)设立“梁思成文物保护史迹展”,系统展示其与古城的不解之缘;如今,正定古建筑内陈列的老照片与测绘图纸,仍让人动容于前辈“与时间赛跑”的坚守。而赵生明烈士以生命护塔的壮举,更与梁思成团队的学术守护遥相呼应,共同化作激励正定人赓续文脉的精神火种——从纸笔间的抢救到血脉中的传承,文物保护已成为这座古城的集体记忆与行动自觉。
自1953年文物保管所成立起,正定便以系统性守护开启了文物保护的征程:从普查登记到发掘修缮,从鉴定展览到制度建设,一步步为古城文物筑牢“安全网”。1961年,隆兴寺、广惠寺华塔等跻身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标志着保护工作进入国家级视野。1963年,梁思成重访正定,目睹昔日濒危的古建筑在新中国重焕生机,难掩激动。
20世纪80年代,正定更以“文化兴县”战略破题,在财政拮据的困境中“勒紧裤腰带”保文物:不仅对隆兴寺实施抢救性修缮以恢复历史原貌,更前瞻性修建停车场等配套设施,让千年古刹成为文旅融合的“活态遗产”。
文脉传承,贵在接力。国家与地方持续投入资金,对古建、城墙、壁画等进行系统性修缮;党的十八大以来,正定以“登得上城楼,望得见古塔,记得住乡愁”为目标,推进古城风貌恢复工程,让“北方雄镇”的历史肌理与当代生活有机交融。从制度保障到民生温度,从抢救性保护到活化利用,正定用七十载实践证明:文物保护从来不是静态的守护,而是一场与时代同行的“文脉接力”。
“历史是城市的骨,文化是城市的魂,历史文化价值正是古城正定的立身之本。”正定古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志敏的话,道出了这座古城的精神密码——尊重历史、珍视文物、赓续文脉,已内化为正定人的全民共识与行动自觉。
如今的正定,正以“历史与现代交融、人文与经济辉映”的独特气质,成为文旅融合的新标杆。在这里,文物不再是冰冷的遗迹,而是可触摸的历史:从古典建筑中读懂“匠心”,从碑帖书画中感知“文心”,从烈士仁人中汲取“丹心”。行走其间,仿佛穿越时空的对话,让千年文明有了具象的既视感。
一座正定城,恰是中华文脉薪火相传的生动注脚——当古塔与街市共生、遗产与生活交融,“保护”与“传承”不再是抽象的概念,而成为流淌在城市血脉中的鲜活力量。
相关推荐: